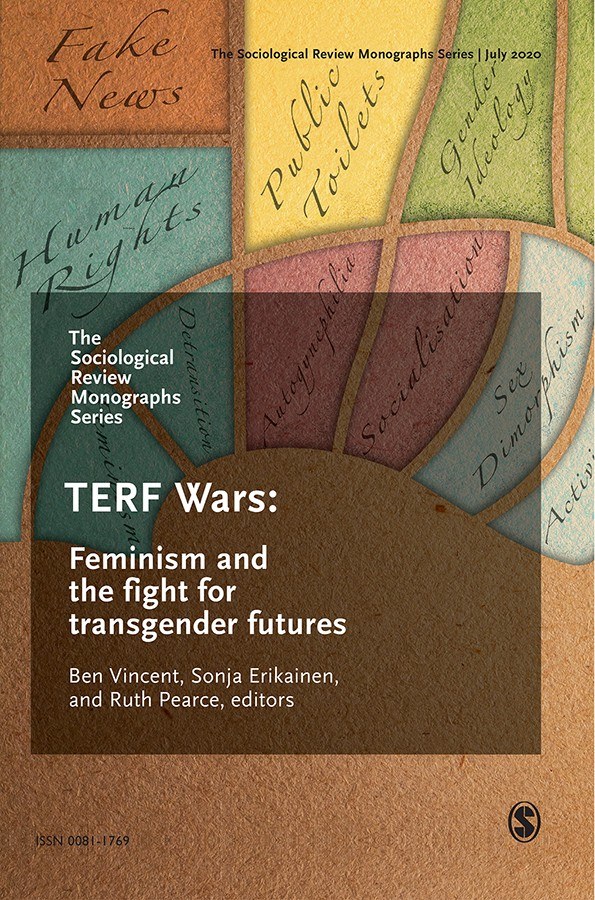
原文:Pearce, R., Erikainen, S., & Vincent, B. (2020). TERF wars: An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8(4), 677–698.
本文作者/本卷编辑:鲁思·皮尔斯(Ruth Pearce)
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 UK)
本文作者/本卷编辑:索亚·埃里凯宁(Sonja Erikainen)
英国爱丁堡大学生物医学,自我与社会中心
(Centre for Biomedicine, Self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本文作者/本卷编辑:本·文森特(Ben Vincent)
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UK)
本文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鲁思·皮尔斯(Ruth Pearce), University of Leeds, Woodhouse Lane, Leeds, LS2 9JT, UK. Email: r.pearce1@leeds.ac.uk
译者:許顓頊(they/them)
关键词(Keywords):排斥性政治(exclusionary politics)、女性主义、性别意识形态、后真相、跨儿女性主义(trans feminism)
关于本译文的几点说明(绝大部分直接复制于译者之前翻译的声明):1.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词汇、结构等),为了保持在这种翻译节奏和风格下阅读仍保持相对顺畅,大部分引用括号中的作者名称不进行翻译,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2.“trans”一词将译为“跨儿”或“跨性/别”、“trans people”翻译为“跨儿者”、“transphobia”译为“跨儿恐惧”或“恐跨”、“transsexual”将译为“跨性”(本译文虽希望保留其历史含义与当代诠释,但完全不希望其作为译文被引入时,被译为“变性”这样在部分中国跨儿与非二元者社群中被视为具有贬损色彩的词汇),而“transgender”译为“跨性别”,读者在阅读时需要仔细思考这几种论述模型的差异;“cis”一词则译为“顺性/别” 3.“female”只译为“女性”,“woman”译为“女人”、“女”、“妇女”,“femaleness”只译为“女性性质”、“womanhood”只译为“女人身份”,“male”与“man”等的翻译则对应,以此类推,“trans woman”译为“跨儿女人”、“trans man”译为“跨儿男人”,当然,这些词的原词会在译文中重复出现以作提醒;4. 本译文中“identity”译为“身份”、“认同”或者“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译为“身份认同”或“认同”、“sex”译为“性”、“gender”只译为“性别”;5. 本译文大部分情况下将保留“TERF”这个词本身,不进行任何展开或者翻译。原文中使用 单引号‘ ’ 作为主要引用和特别用意标记,译文中使用 双引号“ ” 代替。[ ] 内为原文作者补充内容,【】内为译者补充内容。最后,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
在2017-18学年,本卷的一位编辑在英国一所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性别与性存在(gender and sexuality)的课程。这门课程引起了学生们极其积极的反馈。然而,考试结束后,一位监考者(invigilator)与管理部门沟通,对一些学生在回答中使用的语言表示担忧。具体来说,监考者对学生使用“TERF”(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排斥跨儿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这样的缩略词来批评一系列意识形态立场的行为持反对意见,因为TA们认为这个缩写词是一种厌女式的诽谤(misogynist slur)。该课程召集人(convenor)的部门管理者随后询问到该术语是否曾在教学材料中使用过。
事实上,召集人在TA们的任何教学中都没有使用过TERF这一缩写,也没有明确涉及关于女性主义中“支持”或“反对”跨儿(trans)【1】立场的问题。一场关于跨儿女性主义(trans feminism)的讲座特别关注将恐跨(transphobia)理解为厌女(misogyny)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借鉴了朱利亚·塞拉诺(Julia Serano 2007年)等作家的作品,以及对电影的媒体分析,包括《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和《神探飞机头》(Ace Ventura)。是学生们自己把TA们从当代流行话语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TA们的考试手稿中。TA们选择用这个缩略词来指代关于女性主义应该如何概念化以及响应跨儿身份和经验(trans identities and experiences)的一系列日益令人担忧的争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TERF”是TA们在讨论女性主义中的性别、性和包容/排斥政治(the politics of gender, sex and inclusion/exclusion in feminism)时的日常用语(vernacular)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监考者对这个缩略词的反对也表明,在涉及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论时,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乃至辩论的术语本身存在着更广泛的分歧。
【1】我们将 trans (跨儿)作为一个涵盖性术语使用,这与当代使用的 transgender (跨性别)或 trans* (跨儿*)同义,以粗略地描述那些其性别身份认同/自我人格意识(gender identity/sense of selfhood)与出生时的指派(assignment made at birth)(或在生殖器模糊(genital ambiguity)的情况下,稍后提及)不一致的人。我们承认这个词是不完整和不完善的;而且不认同(disidentification)性/性别指派(sex/gender assignment)并不能推断出跨儿身份认同(trans identity)。跨儿身份认同也绝不取决于焦虑不安(dysphoria)、过渡(transition)或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
这则轶事说明着我们作为进行跨儿研究(trans studies)工作的女性主义学者在许多场合都有过的经历。我们并没有寻找 TERF 战争;相反,TERF 战争找到了我们。
我们认为对这一现象的社会学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了解召集人、监考者和学生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全都有效地谈论着不一样的东西却认为都在谈论同一件事(all effectively talked past one another),就很难理解甚至在上述的小分歧中发生了什么。关于跨儿议题、女性主义、反跨意识形态(antitrans ideologies)的激烈辩论,以及各种动因主体(agents)在这些辩论中所使用的语言本身,这些并不仅仅是术语上的争议,也不仅仅是关于性和性别应该如何被概念化的问题。它们也是关于信息的辩论,以及人们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理解(relate to)信息;它们也是关于真相的辩论,以及人们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如何理解真相。我们称之为“TERF战争”的跨儿/女性主义冲突(trans/feminist conflicts)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境况,在这个时代里,公共话语被政治两极化所主导,而虚假资讯的扩散以及对其知识可能无法与个人的文化性常识(individuals’ cultural common sense)产生联系的“专家”的不信任,则加深了这种情况。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当代现象,必须对其进行审视诘问(interrogation),进而了解当前图景(current landscape)。
对排跨修辞(trans-exclusionary rhetoric)的分析为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对意识形态僵化、反证据政治(anti-evidential politics)(包括在学术环境中)的生产(production)提供了深刻洞察,也因为从权力关系中所可以学到的东西(what can be learned about power relations)。谁的声音被听到了,谁被认为是有说服力的,什么被认为是“合理关注(reasonable concern)”以及被谁认为是“合理关注”,还有这些话语如何影响边缘化的群体,这些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要素。
在这篇导言中,我们阐述了这本编辑文集所处的以及所介入的政治、社会和认识(epistemic)语境(context)。我们考虑了当前对跨儿权利(trans rights)的强烈反弹、反跨政治(anti-trans politics)的政治图景(political landscape),以及它们与旧有的性别、女性性质和女人身份之话语(older discourses of gender, femaleness and womanhood)的关系。我们还研究了在女性主义内部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对跨儿现象( trans phenomena)的知识建构、“科学”在排跨论点(trans-exclusionary arguments)中的使用,以及这些被提出的论点所处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图景。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表明为什么在2020年有必要对TERF战争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审视诘问(critical social interrogation),而且还表明为什么这种审视诘问应该是一种跨儿女性主义式的审视诘问(a trans feminist one)。
排跨政治与“性别意识形态”(Trans-exclusionary politics and ‘gender ideology’)
在我们写作的英国背景下,自2017年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宣布保守党政府计划改革《2004年性别承认法案(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GRA)以来,公众的反跨情绪急剧高涨;这一提议同时也得到了英国其它主要政党的支持。尽管 GRA 允许跨儿者(trans people)将出生证明上的性标记(sex marker)从“女性(female)”改为“男性(male)”,反之亦然,但涉及的过程往往被认为是过度医疗化、官僚化、侵害式(invasive)和昂贵的(Hines,2013年)。这是因为改变一个人出生证明上的性标记,除了其它各事项外,还需要以自己偏好的性别生活两年,并且拥有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的医学诊断(或同源的旧术语,如“跨性症(transsexualism)”【2】)。英国的跨儿者可以通过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程序,无需首先更改其出生证明,在几乎所有其它相关记录上更改自己的姓名和性标记(包括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交通管理局(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以及护照办公室(Passport Office)【3】)。这样做通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声明,即声明意图从此以后以新的名字和/或(and/or)性/性别(sex/gender)为人所知。然而,作为一种法律承认,出生证明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具有象征意义。《性别承认法案》(The GRA) 改革计划主要便是由一项提议推动的,该提议允许跨儿者也可以通过自我决定改变其出生证明。这些计划受到了许多跨儿者和 LGBT 组织的欢迎。
【2】 “transsexualism”在且只在这一句话的旧医学偏见、无知、贬损语境中翻译为“跨性症”。其它情况下,译者只会翻译成“跨性”绝不会带上“症状”这样病理化的词汇,同时译者拒绝“变性”等等等一些相关的具有贬损色彩的翻译和词汇,但是译者认为“变性”这一词具有被重新改造的潜能。另外,译者目前完全反对任何带上“症状”或者“症”的词汇翻译。——译注
【3】 如果一个人没有性别承认证明(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或者没有带有后天性别(acquired gender)的出生/领养证明,就需要医生信件才能更改护照上的性标记(sex marker)。
2018年,英国政府就 GRA 改革进行了公众咨询。然而,效果却是对改革建议的强烈反弹。在咨询之前,多个活动组织(campaign organisations)成立,专门抵制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改变出生证明上的性标记(birth certificate sex marker)的机制。包括 A Woman’s Place UK (WPUK)、Fair Play For Women (FPFW)、Mayday4Women、We Need To Talk 和 Lesbian Rights Alliance 在内的组织在英国各地召开会议,建立了一个新的排跨女性主义运动(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t movement),这个运动也通过推特(Twitter)和妈妈网(Mumsnet)“女性主义聊天(feminist chat)”留言板等数字平台在网上迅速扩大。而这些团体的活动和观点也被媒体广泛报道。在撰写本文时,GRA 改革尚未实现(materialised)。2020年4月22日,妇女与平等部长(Women and Equalities Minister)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向妇女与平等特别委员会(Women and Equalities Select Committee)发表讲话,在提到 GRA 改革时,她表示将在2020年夏季报告该法案的未来。特拉斯强调了与此相关的三个优先事项:对单性空间(single-sex spaces)的“保护”(错误地暗指 GRA 与可能使用这些空间的人已经有或将要有相互作用);“维持系统中适当的制约与平衡”(暗指一个对跨儿成人的自主权的把关控制(gatekeeping)模型);以及“保护”18岁以下的人免受“TA们可能做出的决定”的影响,这引起了对18岁以下跨儿者获得与性别相关的医疗保健的本已受到高度限制的使用机会的严重担忧,而且隐含着对所有年轻人身体自主权的威胁。
为了理解这种强烈反弹(backlash)的性质,有两点值得解读,即 WPUK 和 FPFW 这样的团体到底反对和拥护什么。第一点是有关于性(sex)和性别(gender)是如何被操作化的(operationalised):这些组织所调动(mobilised)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女人的基于性的权利(women’s sex-based rights)”,这个概念的使用方式强调了性(作为“生物的”或物质的实在(material reality))与性别(作为社会角色或意识形态)的区别(distinction)。反对性别自决(gender self-determination)的这些组织不仅认为性和性别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而且认为英国的法律如 GRA 和《2010年平等法(the Equality Act 2010)》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阐释,即跨儿女人(trans women)应被理解为“男性(male)”,跨儿男人(trans men)应被理解为“女性(female)”,非二元者(nonbinary people)应被理解为隐性妄想(implicitly delusional)(Fair Play for Women,2017年)。也就是说,这些组织的观点是,虽然“性别”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性”是不可改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立场忽略了数十年来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性别和性是话语性地共同构成的(discursively co-constituted)(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会再提到),以及“性”和“性别”在英国法律中实际上并没有被独立地定义(Jenkins & Pearce,2019年;Sandland,2005年)。【4】
【4】 虽然“性(sex)”和“性别再指派(gender reassignment)”在《2010年平等法(the Equality Act 2010)》中是单独的受保护特征(separate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但这些类别即使被命名为 “性别(gender)”和“性再指派(sex reassignment)”,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生效发挥作用。前一类用于防止——基于个人作为女人或男人的状态身份(status)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措施,而后一类用于防止——基于个体经历到的(undergone)社会的 和/或 物理的 性/性别过渡(social and/or physical sex/gender transition)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措施。
第二点是有关于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主张的是为了使什么成为可能。抵制自我决定的组织话语般地(discursively)将其定位为是(position it as)“危险的”,认为它使“男人(men)”(这个范畴经常被假定为包括跨儿女人 trans women 和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 male 的非二元者 non-binary people)能够不受约束地进入女人专用的空间(women-only spaces)。跨儿者和盟友(allies)经常将这种方式的倡导者描述为 “TERFs”,因为TA们倾向于支持将跨儿女人/女孩(trans women/girls)排除在女人的厕所、更衣室、强奸危机处理中心(rape crisis centres)、庇护所和女性主义团体等这样的空间之外。
对拟议的 GRA 改革的强烈反弹,以及在英国形成的与此改革相关的排跨女性主义运动,并不是凭空(in a vaccum)出现的。相反,它们是具有国际层面的更广泛的排跨政治气候(trans-exclusionary political climate)的语境表达(contextual expression)。例如,201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台法律,要求个人使用与其“生物性别(biological sex)”相对应的公共厕所。其目的主要是禁止跨儿者使用与其性别相一致的厕所设施。随后,美国其它州也提出了类似的法律(所谓的“厕所法案 bathroom bills”)(Barnett 等人,2018年)。反跨“厕所法案”的倡导者认为,这些法案是为了保护顺性/别【5】女人(cis women)的安全,她们可能会成为跨儿女人(trans women)和非二元者(non-binary people)伤害的受害者,并且TA们反过来又被(隐含地或明确地)定位为是“身份认同为(identify as)”女人的 “男人”。
【5】 顺性别(cisgender)(或 cis)是一个描述性术语,指的是 非跨儿 和/或 其性别经验与其出生时被指派性别相符的人。这个词早在1992年就开始使用,它已经取代了“非-跨儿(not-trans)”、“出生-女人/男人(born-women/men)”、“生物女人/男人(biological women/men)”或“自然女人/男人(natural women/men)”等术语,最终起到了中和作用(neutralising function)。而为了抵制这种做法,许多“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活动家(activist)声称,顺性/别(cis)(就像 TERF 一样)是一种诽谤(slur)。对于跨/顺二元(trans/cis binary)的局限性的认识,已在学术上被表达阐述(比如 Enke,2013年)。
这种争论是较早的性/性别本质主义话语(sex/gender essentialist discourses)的当代表现形式:长期以来,跨性/别女人(trans women)被定位为是对顺性/别女人(cis women)安全的威胁,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因为跨性/别女人的身体在话语上(discursively)被与危险的男性性存在【或译“性欲望”】(male sexuality)以及潜在的性狩猎(sexual predation)联系在一起(Westbrook & Schilt,2014年)。女人专用设施(Women-only facilities)如厕所往往被定位为“安全空间(safe spaces)”,给予(顺性/别)女人保护,使其免受基于性别的伤害(gender-based harm),尤其是性暴力(sexual violence)(见 Jones & Slater,本合集)。然而,这种厕所“安全(safety)”的概念是围绕着(顺性/别)女人身体的更广泛的保护主义政治(protectionist politics)的一部分,其功能是为了保卫白人女性脆弱性(white female vulnerability)这种理想化概念(idealised notions)(Patel,2017年;另见 Koyama,本合集)。将跨性/别女人作为是对顺性/别女人构成危险,这一文化定位,依赖于——(顺性/别,隐含地白人(implicitly white))女人相对于(顺性/别)男人而言必然是脆弱的(fragile)——这一性别化的概念化(gendered conceptualisations),同时男人又被概念化为具有更优越的身体(和性)勇猛(physical (and sexual) prowess)。通过将(顺性/别、白人)“女性(females)”定位为一个特别地(uniquely)容易受到“男性的(male)”暴力(特别是 “生物”男性的性暴力(‘biological’ male sexual violence))伤害威胁的类别,围绕厕所使用权的排跨论点——包括那些自称为女性主义团体提出的论点——为长期以来将(白人)女人定位为需要保护(由男人来保护、来自男人的保护 by men, from men)的“较弱的性(weaker sex)”这样性别化的(gendered)且厌女的话语(diiscourses)提供了支持。
这些话语具有着种族主义的潜在寓意,因为作为保护对象的女人所隐含的白人性质(the implicit whiteness of the women)意味着种族化的(racialised)且特别是黑人女人(Black women)和非二元者(nonbinary people)更有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男性气质式的(dangerously masculine)(Patel,2017年)。这是由于长期存在的殖民遗产,一直以来将被种族化的女人(racialised women)定义为是非女性气质的(unfeminine)或是“男性气质的(masculine)”,与白人女人所被假定的“自然(natural)”女性气质(femininity)形成鲜明对比(见例如 McClintock,2013年)。种族化的女人(顺性/别者和跨性/别者都一样)、非二元以及间性者(non-binary and intersex people)都特别容易被渲染为“性别嫌犯(gender suspect)”,这是由于这样的话语,即有色人种身体被定位为与白人身体规范(white body norms)相关的性别偏常僭越(gender deviant)(Gill-Peterson,2018年;Snorton,2017年)。此外,将跨性/别女人(trans women)和非二元者(non-binary)定位为是对顺性/别女人(cis women)的“威胁”的话语,掩盖了(elude)——(白人)顺性/别女人在这种语境下宣称自己处于易危脆弱地位(a position of vulnerability)的能力(ability)且这能力本身就反映了(白人)顺性/别女人相对于跨性/别女人(以及所有性别的种族化主体 racialised subjects of all genders)所拥有的权力。一个人被承认为(recognised)或被授予(awarded)一个“易危脆弱(vulnerable)”之地位的能力是以白人性和性别规范性(whiteness and gender normativity)作为条件的。往往是跨性/别女人和非二元者,特别是有色人种跨性/别女人和有色人种非二元者,在女人专用(women-only)空间中最容易受到(vulnerable to)物质上的(in material terms)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见 Jones 和 Slater,本合集)。是不成比例的顺性/别者(包括女人和男人),对跨性/别女人构成危险和实施暴力,而不是相反(Bachman & Gooch,2018年;Hasenbush 等人,2019年)。是通过这种方式,排跨女性主义政治(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t politics)才得以抹除各种性别化的和种族化的暴力形式(forms of gendered and racialised violence)。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许多(但不是全部)跨儿者和盟友将排跨女性主义的活动者们(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t campaigners)描述为“TERFs”,但这些活动者们本身普遍反对这个缩写。近年来,许多人更愿意称自己为“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这个词并不是指对性别进行批判性方法介入(critical approach),而是强调着主张呼吁“生物定义的(biologically defined)”女性性质(femaleness)和女人身份(womanhood)的概念,而不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 identity)和性别的社会概念(social concepts of gender)。除了攻击跨儿者根据其性/性别呈现(sex/gender presentation)使用公共厕所的权利,“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还批评社会发展,如包容LGBTIQ的(LGBTIQ-inclusive)学校教育以及媒体对跨儿者积极的表征体现(representations)。TA们越来越多地认为,这种发展是TA们所称的“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的结果(例如,见 4thWaveNow,2019年)。
“性别意识形态”之语言起源于右翼基督徒中的反女性主义和反跨话语,同时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担当着主要的成核催化剂(nucleating agent)(Careaga-Pérez,2016年;Kuhar & Paternotte,2017年)。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众多美国、欧洲和非洲国家的极右翼组织和政客所采纳。TA们将性别平等主义(gender egalitarianism)、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和 LGBTQ+ 权利定位为以跨国大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以及如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代表的“全球精英(global elites)”对传统价值的攻击(Korolczuk & Graff,2018年)。在这个语境下,“性别”被用来作为身份政治和社会可塑性观念(notions of social malleability)的替代:“性别(Gender)为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了剧场舞台 ... 一场重新定义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竞赛,在其中‘性别意识形态’具现了(embodies)所谓的进步行动者(progressive actors)的诸多缺陷”(Kováts,2018年,第535页,强调着重标记为原文所加)。
马洛里·摩尔(Mallory Moore 2019年)追溯了“性别意识形态”在“性别批判”语境中的首次出现:是一个2016年排跨女性主义网站 4thWaveNow 上一篇博文的回复评论,其中该博文分享了保守派倡导团体美国儿科医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不要与专业机构美国儿科学会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混淆)的材料。从那时起,这个概念在排跨女性主义话语中的流传越来越广,特别是自从“性别批判”活动家(activist)斯蒂分尼·戴维斯-阿莱(Stephanie Davies-Arai)(其曾在 4thWaveNow 上接受采访和介绍过)在反跨活动者(anti-trans campaigners)参加的一个伦敦会议上使用这个概念之后(Singleton,2016年)。
然而,“性别意识形态”的实际含义(以及反女性主义者(anti-feminist)对“性别主义(genderism)”和“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等术语的使用)尚未得到明确界定:正如伊丽莎白·科罗祖克(Elżbieta Korolczuk)和阿格涅斯卡·格拉夫(Agnieszka Graff)(2018年,第799页)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术语已经成为了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s),成为了道德败坏(demoralization)、堕胎、非规范的性存在/性欲望(non-normative sexuality)和性困惑(sex confusion)的灵活同义词(flexible synonyms)”。
这使得它们成为围绕着传统性/性别观念的崩溃而唤起编造(conjuring)道德恐慌的有效工具,例如,跨儿解放运动(trans liberation movement)日益增加的关注度(visibility)就证明了这一点。梅格-约翰·巴克(Meg-John Barker 2017年)观察到英国媒体内部对跨儿之存在(trans existence)的道德恐慌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跨儿者(trans people)既被指责为瓦解了(dismantling)又被指责为强化了(reinforcing)当前的性别体系,而跨儿女人作为女人的状态身份(status)被质疑的理由在某些语境下是根据生物学而提出的,而在其它语境下则归咎于社会化(socialisation)。所被提议的解决方案往往是在法律和政策中将“性别(gender)”问题抛之脑后,而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律上以“出生的性(birth sex)”为基础来定义女人(women)和男人(men)。2020年,这在一些司法行政辖区(jurisdictions)成为立法现实(legislative reality)。在3月,美国爱达荷州禁止跨儿者更改出生证明,在4月,匈牙利独裁者维克托·欧本(Viktor Orbán)(一位直言不讳地批评“性别意识形态”的人)的政府就在极右翼领导人被正式授予(granted)依法令治理(rule by decree)权力的同一天,就开始在法律上重新定义 性(sex)。
最终,跨儿和非二元者(trans and non-binary people)越来越高的社会接受度已对“女性性质(femaleness)”和“女人身份(womanhood)”这两种不可改变的(immutable)、生物衍生的(biologically derived)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s)提出了挑战。对此,“性别批判”反对立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富含情绪的(emotionally loaded)、反动保守(reactionary)的反应,以重申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导致了诸如“女人基于 性 的权利之宣言(Declaration of Women’s Sex-Based Rights)”(见 Hines,本合集)这样的干预,且这实际上有效地呼应了极右、反女性主义行动者(far-right, anti-feminist actors)的要求。
跨儿/女性主义关系(Trans/feminist relations)
虽然跨儿主体性(trans subjectivities)和女性主义有时被定位为对立的,特别是被“性别批判”作家,但这种框定两者之关系的方式并不是对女性主义思想之图景(landscape)的主导理解(也不是准确理解)。这种关系的起点往往被认为与詹妮斯·雷蒙德(Janice Raymond)的《跨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1979年)的出版相关,该书将跨儿女人(trans women)定位为是潜入女人空间(women’s spaces)、侵占女人身体的暴力男性主体(male subjects)。例如,埃莉诺·麦克唐纳(Eleanor MacDonald 1998年, 第3页)将雷蒙德的作品描述为“关于跨性主义(transsexualism)议题的经典(且直到最近,几乎是独有专属的 exclusive)女性主义声明”。然而,雷蒙德对跨儿者(trans people)的描写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独有专属的(exclusive)对跨儿议题的女性主义论述(feminist account)。事实上,Susanne Kessler(苏珊·凯斯勒)和温迪·麦肯纳(Wendy McKenna)的《性别:一种民族学方法论的方式》(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1978年)早在前一年就已出版。这部著作广泛地讨论了跨性主义(transsexualism),不是从像雷蒙德那样把跨性主义-作为-厌女(transsexualism-as-misogyny)的角度,而是将其作为我们都在“做(doing)”或表演性别(performing gender)的例子。
麦克唐纳(MacDonald)自己对跨性主义(transsexualism)的态度并不是敌对的,而是像凯斯勒(Kessler)和麦肯纳(McKenna)(1978年)一样,对跨儿视角(trans perspectives)“可能对理解性别经验(gender experience)、性别关系或女人受到的压迫(women’s oppression)有什么贡献”感到好奇(MacDonald,1998,第4页)。虽然麦克唐纳注意到,许多女性主义作家忽视了跨儿现象(trans phenomena),因为它们表面上的罕见(apparent rarity)并且与医学文献相关联,但当她提出这一观点时,应对跨儿议题的女性主义方法(feminist approaches)已经开始改变。到了1990年代后期,在许多女性主义论述中,跨儿主体性和性别多样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解性别的社会建构的更普遍的切入点。这特别是由于后现代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出现——尤其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年)的介入,将性和性别两者各自的二元论观念(binary notions of sex and gender)理论化为是文化构成的(culturally constituted)——以及跨性别研究(transgender studies)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1990年代的涌现(Stryker & Aizura,2013年)。其也是延续着跨儿者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日常参与(everyday involvement)——几十年来这在许多国家成为现实(Cutuli,2015年;Enke,2018年;Garriga-López,2016年)。
主流女性主义思想普遍认为,女性主义与跨儿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探究性别关系与性别系统(gender relations and systems)的建构和表现形式的核心位点(locus)。例如,《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2011年的种族与跨性别研究专刊的序言开篇就称,“一段时间以来,女性主义者都一直与跨性别主体性(transgender subjectivity)给性存在和性别二元论(sexuality and gender binaries)带来的挑战进行斗争,尤其是在对‘女人(woman)’这一范畴的理解上”(Richardson & Meyer,2011年,第247页)。然而,理查森(Richardson)和Meyer(梅耶)并没有暗示这些斗争涉及到,女性主义是否可以是跨儿包含的(trans-inclusionary),又或者跨儿存在(trans being)是否威胁到女性主义实践(feminist praxis)。相反,TA们强调了在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中将边缘化声音作为中心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处理(address)在跨性别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性(whiteness)的必要性,这两个议题在今天仍然是高度相关有价值的(highly relevant)(Green & Bey,2017年)。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相对多产的排跨激进女性主义学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scholars)(如 Jeffreys,1997年、2014年),但TA们一般来说都没有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对话,尤其是由跨儿女人和跨儿包含政治的盟友(allies with trans-inclusionary politics)所撰写的理论(豪斯曼 Hausman 除外,1995年)。 相反,排跨女性主义者普遍都不参与(sat outside)长达数十年的跨儿/女性主义生产(trans/feminist productivity),部分是因为TA们深信(conviction)共同的“女性性质”/“女人身份”(‘femaleness’/‘womanhood’)的(生物学)观念是女性主义所必需的,而跨儿身体和主体性对这些观念构成了威胁(正如 海恩斯 Hines、小山 Koyama、卡雷拉-费尔南德斯 Carrera-Fernández 和 德帕尔马 DePalma 在这本合集中所讨论的)。
在对当前排跨女性主义政治的图景(landscape)的理解中,不同方(parties)在辩论中使用的术语是核心,而术语也构成了对分析排跨话语的挑战。这是因为语言被刻意用来包含、排斥 和/或 表示权力关系:例如,跨儿包含女性主义(trans-inclusive feminist)作家倾向于使用“跨儿女人(trans women)”一词,因为这意味着(implies)跨性别女人是女人的一种(就像“同性恋女人 gay woman”)。然而,“性别批判”作家一般使用“transwomen”【6】同时避免使用“顺/性别(cis)”一词,因为这会(隐含或明确地)将跨儿女人(trans women)从一般的“女人(women)”范畴中排斥出去——通过将“女人(women)”与“顺性/别女人(cis women)”合并在一起(conflating)。
【6】 此处没有这个词的合适翻译,读者可以注意的是,在日常语言中,许多人使用“transwomen”一词的含义,与 GC feminists 或者 TERFs 所使用的含义截然不同。而这些人并没有恶意,译者认为这类词语有着各种被改造重新利用的可能。——译者
类似的争论围绕着“TERF”这个缩写,它最初是在2000年代末被一些顺性/别女人( cis women)用来明确区分她们自己的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与排跨取向的论述方式(trans-exclusionary approaches)(Smythe,2018年)。“TERF”现在被许多跨儿包容的女性主义者(trans-inclusive feminists)所采用,而被排跨活动者(trans-exclusionary campaigners)拒绝。反对‘TERF’这个缩写词的个人往往认为它相当于一种厌女式的诽谤(a misogynist slur),就像本文开篇梗概中的外部检查者(external examiner)情况一样。当然,TERF(就像“cis”一样)经常被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主义者(cis and trans feminists)在网上愤怒的评论中使用,要么是指责(如“你是个TERF you’re a TERF”),要么是辱骂(如“滚开TERF fuck off TERF”)。然而,理解和解释论述(account)这里的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是很重要的。在上述例子中,被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及其盟友试图识别并表达对于一种有危害的意识形态的愤怒或挫折,而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由那些在制度上享有特权(systemically privileged)并且这符合TA们的利益的顺性/别者(男人 men 和女人 women)所推动的。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不需限定条件(without qualification)的有帮助的过程。例如,一个善意的但知之甚少(poorly-informed)的人可能会被不公平地贴上 “TERF”的标签,由于TA们缺乏对跨儿生活/生命之现实(the realities of trans lives)的认识(awareness)和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TERF”实际上充当着诽谤的功能(functions as a slur)。例如,克里斯托弗·戴维斯(Christopher Davis)和伊林·麦克里迪(Elin McCready)(2020年)就认为,虽然这个缩写可以被用来诋毁(denigrate)一个特定群体,但这个群体是由特定的意识形态(chosen ideology)所定义的,而不是由固有属性(intrinsic property)所定义的(比如,这情况与跨儿者 trans people 或女人 women 相反的)。而正是这种对一个由固有属性定义的群体的诋毁(denigration)才是构成诽谤(slur)的必要条件。此外,在“TERF”一词的情况中,诋毁行为之运作并不是为了(does not function to)从属于(subordinate within)某种权力关系结构(structure of power relations)之内(这与错误性别化别人的行为(misgendering)和性歧视式诽谤(sexist slurs)如“贱人(bitch)”【7】相反)。
【7】读者可以如此理解,在这里举的例子中,显然,“bitch”一词是高度语境化的,其完全可以是赋权和积极的,也可以是充满着对性工作者恶意(whorephobia)、充满着对各种形式的性行为的侮辱、对各种性开放关系的侮辱、充满着父权体制下对性行为/性欲望/性存在(sexuality)各种规范、各种性别规范等等含义的诋毁。——译注
更令人困惑的是,关于“TERF”这个缩写词的适当使用和实际指称(actual referent(s) )的存在着争论。近年来,“TERF”一般而言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跨儿恐惧(transphobia)或恐跨个人(transphobic individuals),失去了它的原意(排跨激进女性主义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跨儿社群和其盟友在反TERF的语言 何时会 以及 如何会 过火走得太远 这一问题上往往存在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跨儿女性主义作家批评了使用过度暴力的意像(excessively violent imagery)的干预措施,尤其是当这种意像主要是由男性(male) 和/或 顺性/别个人(cis individuals)进行宣传(propagated)时。例如,贝丝·德斯蒙德(Beth Desmond 2019年)批评了一段病毒般疯传的视频(viral video),在其中一个男性(male)电子游戏角色反复刺伤被贴上“TERF”标签的女性(female)角色,贝丝谈论到“跨儿女人(trans women)从一个乐于对女人(women)施加暴力的男人(man)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与激进女性主义运动(radical feminist movements)相关的反跨性别运动者(anti-trans campaigners)公开与反女性主义组织(anti-feminist organisations)结盟。例如,从2017年开始,美国团体妇女解放阵线(Women’s Liberation Front 缩写 WoLF)与保守派组织传统基金会和家庭政策联盟(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Family Policy Alliance)合作,这两个组织都以支持传统的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和反对堕胎权利、反对全面的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以及反对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而闻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像 WoLF 这样的组织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t)”(由此就得出是“TERF”)组织。然而,重要的是要承认,这些组织确实(do)明确地动用了妇女解放(women’s liberation)的语言,并有效地体现代表了激进女性主义作家如雷蒙德(Raymond 1979年)和杰弗里斯(Jeffreys 1997年)的遗产。女性主义者——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者——必须与之【即这样的遗产,译注】抗衡:由此首先创造了“TERF”这样的缩写词。因此,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试图特别关注与女性主义相关联的排跨意识形态和行动(trans-exclusionary ideology and action),而不是试图围绕什么才算作或者什么不“算作(count)”女性主义介入(feminist intervention)来划定界限。
因此,TERF战争最好被理解为女性主义内部(而不是反对女性主义)的一系列复杂的话语和意识形态之争(discursive and ideological battles)。女性主义历史以及关于语言的辩论两者是这个争论图景(contested landscape)的核心。“真相(truth)”和“中立(neutrality)”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些概念与排跨女性主义话语(trans-exclusionary feminist discourses)一起被用来破坏跨儿行动主义和研究(trans activism and research)。
后真相时代的“性别批判”女性主义(‘Gender critical’ feminism in the post-truth era)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时代,传统的专业知识(expertise)概念以及事实的认识状态(epistemic status)正在分崩离析,所谓的假新闻(fake news)尤其是在数字空间的假新闻激增泛滥就是例证(Marres,2018年)。随着空前数量的人能够接触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那里TA们可以阅读和传播各种信息,而众多不同定位的知识主张(differently positioned knowledge claims)现在在数字空间中共存。实际上,有人认为,许多人正在放弃传统的证据标准,而倾向于另类的知识和信仰(Lewandowsky 等人,2017年)。这种“后真相”的环境经常被“性别批判”作家所引用,TA们认为跨儿者的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被媒体和立法机构(legislative bodies)以难以反对的方式所认可背书(Brunskell-Evans & Moore,2018年;Davies-Arai,2018年;Moore,2018年)。例如,海瑟·布朗斯可-埃文斯(Heather Brunskell-Evans)和米歇尔·摩尔(Michele Moore)(2018年,第5页)声称,年轻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是“生在错误的身体里”的想法是“被跨性别游说者(transgender lobbyists)在质疑挑战被沉默(challenge is silenced)的文化氛围中无休止地推动的”。其它人则指出了“沉默”的因素,比如“害怕批评或争议”,特别是围绕“恐跨偏执行为(transphobic bigotry)的指控”(Kirkup,2019年)、场地在收到关于恐跨内容的投诉后取消了活动预订(Doward,2018年),以及个人拒绝与其认为是恐跨的人一起参加公众讨论(Bindel,2018年)。有断言称(assertions)反跨活动者(通常被定位为 “女人” 和/或 “女性主义者”,尽管许多就这些问题撰写文章的记者是男人,以及/或者 供稿给历史上向来不赞成女性主义观点的出版物)面临着反对,尤其是因为TA们对真相的恪守承诺。例如,朱利·宾德尔(Julie Bindel 2018年)在为《Quillette》撰写的文章中坚持认为,“像我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拒绝接受阴茎是女性身体部位(female body part)的观点,或者拒绝说出奥威尔式的咒语(Orwellian mantras),将跨儿女人(trans women)与生物女性(biological females)完全等同起来”。
然而,在主流媒体以及在横跨各政治路线举行的政治活动中,似乎都能清晰地听到“沉默(silencing)”的说法。在英国,包括《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卫报》(The Guardian)、《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和《星期日邮报》(The Mail on Sunday)在内的左派和右派媒体都经常发表“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的观点。仅在谷歌搜索2018年《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发表的关于“跨性别(transgender)”的文章,就会有约230个结果,标题包括“女童子军领导人因质疑跨儿政策而被开除”(Girl Guide leaders expelled for questioning trans policy)、“挑选性别是恶魔般的,男教士写道”(Picking and choosing gender is demonic, writes churchman)等等。英国议会和苏格兰议会也举办了多场“性别批判”活动,分别由保守党、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政客主持。
“性别批判”和基督教保守派作家都经常将跨儿社群(trans communities)以及包容性女性主义(inclusive feminisms)定位为庞大统一的“邪教”(a monolithic ‘cult’)(如 Davies-Arai,2018年;Hendley,2019年;Trinko,2019年)。通常情况下,这种断言依赖于暗示(implication)而非论证(argument):例如,斯蒂分尼·戴维斯-阿莱(Stephanie Davies-Arai 2018年,第30页)所写的“对儿童的跨性别实验”(the transgender experiment on children)中包括了一个标题为“招募到邪教?”(recruitment into a cult?)的章节,但完全没有解释 如何/为什么 跨儿社群可能被理解为邪教。相反,她认为,英国运营(run)跨儿青年群体(trans youth groups)的组织,包括 Gendered Intelligence 和Mermaids,通过为“弱势青少年们提供TA们正在寻找的‘部落(tribe)’ ... [TA们] 也许会第一次在这些群体中找到认可和归属感,只要TA们身份认同自己为跨性别(transgender)” 从而 “验证生效(validate)以及强化了(reinforce)一种跨性别身份认同(a transgender identity)”(Davies-Arai,2018年,第31页)。在为《女性主义趋向》(Feminist Current)撰写的一篇阅读量很高的博文中,艾丽西亚·亨德利(Alicia Hendley 2019年)补充道:
...虽然我不愿意称跨儿行动主义(trans activism)为“邪教”,但我意识到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绝对拒绝允许任何人批评问题;沉默、抹污(smearing)和排挤(ostracizing)那些对跨性别主义之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ransgenderism)提出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给TA们贴上“恐跨”的标签);以及迫使个人(从父母到卫生专业人员)不加思考地(blindly)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有些人是“出生在错误的身体”,而“修复(fix)”这一错误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医疗干预。
重要的是,这些说法完全没有涉及到被广泛记录着的跨儿知识、社群和行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这方面的讨论见】如 Boellstorff 等人,2014年;Ekins & King,2006年;Halberstam,1998年;Prince,1973年)。例如,苏利耶·门罗 (Surya Monro 2007年)通过在印度和英国的跨儿社群内进行为期10年的定性访谈和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论证了跨儿者对性和性别的看法是多样化的。这些观点包括以身体为中心或去中心(centring or de-centring the body),支持或反对废除性别(gender abolition)或“去性别(degendering)”,依赖女性(female)和男性(male)的认同(identifications)和/或 寻求占据一个非二元空间(non-binary space)。跨儿者也可能根据TA们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处境,策略性地将自己定位为是较多僭越离轨的(transgressive)或较少。例如,僭越离轨的性别表达(gender expression)可能导致一个人失去自己的支持网络,或成为被赶出家门的理由。这可能会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对出柜的期望或对僭越性的超越规范的期望(coming out or transgressing transnormative expectations)的代价太高。因此,门罗(Monro)主张一种“性别多元主义的(gender pluralist)”跨儿身份模型(model of trans identity),承认多种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方式;这种模型最终反映在许多跨儿空间(trans spaces)的社区动态中(Pearce,2018年;Pearce & Lohman,2019年)。同样,众多跨儿女性主义作家广泛批判了所谓的“错误身体(wrong body)”叙事(如 Bettcher,2014年;Lester,2017年)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跨性/别身份(trans identity)的病理化的(pathologising)顺性/别医学模型(cis medical models)(Gill-Peterson,2018年;Riggs 等人,2019年;Stone,2006年)。
因此,“性别批判”的解释论述(‘Gender critical’ accounts)往往与跨儿者理论化、认同(identify)和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方式相冲突。这并不是说“性别批判”的说法总是完全不准确。例如,艾丽西亚·亨德利(Alicia Hendley 2019年)所认为的,在“跨性别行动主义”中,存在着“对那些提出关于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意识形态的问题的人的沉默、抹污和排挤。”亨德利没有确切地描述这些问题是什么,但可以很合理地想象,一个特定的质问(given enquiry)可能会被亨德利认为(perceived)是一个无辜的询问(innocent enquiry),但(取决于问题的框架)可能会被跨儿者感受为(experienced)是恐跨行为。例如,亨德利隐含地质疑跨儿青年有自杀念头(ideation)和自杀企图的高风险这一事实,并将跨儿行动主义(trans activism)中的这一援引描述为“恐吓策略(scare tactics)”。对于在年轻时经历过多个朋友自杀身亡的跨儿活动家来说,这可能会很合理地被视为是一个恐跨式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更普遍的跨儿自杀倾向(trans suicidality)的实证性证据(empirical evidence)(Adams & Vincent,2019年;Pearce,2020年)。因此,TA们可能会寻求关闭讨论或避免未来与亨德利接触,而不是继续讨论。虽然这种差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不同但共存的知识形式引起的认识问题(epistemic problem),但亨德利和她的跨儿对话者(trans interlocutor)的不同视角观点也可以从虚假资讯(misinformation)和权力的角度来理解(Lewandowsky 等人,2017年)。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坚持认为关于性、性别和跨儿现象(trans phenomena)存在着一种可定义的“(跨)性别意识形态 (trans)gender ideology”,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这种观点的继续流传也可以被视为恐跨的(transphobic),因为它涉及到是对跨儿者的不准确(往往是偏见)的看法,而不是致力于真正的对话。
即使是在“性别批判”作家似乎参与到跨儿理论(trans theory)的地方,这些参与一般来说都是局部的。例如,米歇尔·摩尔(Michele Moore 2018年,第225页)批评了一个“障碍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和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的拟议联合(proposed coalition)”,但没有解释这个联合可能是什么样的,并且没有引用除了《跨性别研究读本·二》(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Stryker & Aizura,2013年)的导论文章之外的任何跨尔作家。越来越多的关于障碍(disability )与跨儿理论和行动主义(trans theory and activism)之交叉(intersections)的文献(如 Baril,2015年;Chung,2011年;Mog & Swarr,2008年;Puar,2014年;Slater & Liddiard,2018年)在摩尔的解释论述中完全没有。而一些同情“性别批判”立场的作家也对跨儿作者的论点提出了完全不准确的说法。例如,大卫·皮尔格林(David Pilgrim 2018,第309页)认为,“跨儿者个体的个人脆弱性(personal vulnerabilities)与TA们的集体社会定位(collective societal position)之间的模糊界限,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会促使跨儿活动家及其支持者拒绝接受这些性别批判的女性主义论点,同时认为这些论点是偏执和‘恐跨的’(Pearce 2018)”。克莱拉·格里德(Clara Greed 2019年,第912页)陈述道,“跨性别和性别非二元(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binary)厕所使用者可能会发现 GNTs [性别中立厕所 gender neutral toilets] 为TA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替代选择( ... Pearce,2018年)”。这些论点实际上在皮尔斯文章(Pearce 2018年)中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皮尔格林和格里德似乎只是选择皮尔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跨儿作者(token trans author)来引用,而没有读过她的作品,这就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在对排跨议程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rans-exclusionary agendas)中所提出的这类真相主张(truth claims)。
在排斥性政治中调动“科学”和“中立”(Mobilising ‘science’ and ‘neutrality’ in exclusionary politics)
在排跨论点中使用(和滥用)真相主张(truth claims)的做法,既引起了人们对被用于证明这些论点的证据形式的质疑,也引起了对自称的女性主义者(self-proclaimed feminists)与历史上向来“性别保守的(gender-conservative)”组织之间正在形成的认识/知识联盟(epistemic alliances)的质疑(Krutkowski 等人,2019年)。正如上文所述,“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的论点往往与几十年来女性主义对“女人身份(womanhood)”和“女性性质(femaleness)”的本体论和认识状态(ontological and epistemic status)的理论化(theorising)相悖(并忽视这些理论化)(另见 Hines,2019年)。性别学者(如 Butler,1990年;Laqueur,1990年;Snorton,2017年;Warren,2017年)已经表明,对性(sex)的生物概念化(biological conceptualisations)如何被更广泛的性别化(gendered)以及殖民和种族化规范(colonial and racialised norms)所中介,这些规范指导着(direct)被归赋于(ascribed to)不同女人(women)和男人的社会定位(social positions),包括一个人在一开始声称自己是“男人”或“女人”的能力。西方殖民叙事不仅将被殖民的种族化主体视为非人类(less than human),而且还将(以欧洲白人异性规范 white, European heteronorms 来定义的)“女人身份(womanhood)”和“男人身份(manhood)”框定为人类文化的特征,而被殖民主体因其“原始(primitive)”地位状态(status)被视为无法复制。因此,TA们充其量仍是女性(female)和男性(male),但并没有被赋予(granted)女人和男人的身份状态(the status of women and men)(McClintock,2013年)。这意味着,女性(female)和男性(male)本身就是社会构成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下,对不同的人来说,含义也不同。此外,女性主义科学研究(feminist science studies)业已表明,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语言出现在整个当代生物学中(如Birke,1999年;Haraway,1991年;Hubbard,1990年),因此值得区分作为生物体物质组织的生物学(biology as organisms’ material organisation)和作为关于那生物体的科学话语的生物学(biology as the scientific discourse about that organism)(Birke,2003年)。在呼吁“女性性质(femaleness)”作为“生物‘真相’ ”时,“性别批判”的论点未能解释 性差异(sex difference)本身是如何通过——被关于“女人身份(womanhood)”和“男人身份(manhood)”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观念(gendered and racialised ideas)所形塑的社会生物话语(socio-biological discourses)——而被生产为是二元的(been produced as binary)(Fausto-Sterling,2000年;Laqueur,1990年)。然而,目前,“性别批判”女性主义团体正在积极地重新主张“女性性质(femaleness)”是一种固定的、不可否认的生物现实(biological reality),并认为无论跨儿女人(trans women)是否是(社会式地 socially)女人(women),她们都不可能是“女性(female)”,因为女性性质(femaleness)需要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定生物构成(particular biological makeup)(见 Hines,2019年)。
关于性差异(sex difference)的本质主义论点并不局限于“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女性主义团体,也不局限于专门围绕“跨儿身体(trans bodies)”的讨论。它们还延伸到了更高层次的政治和政策话语中。例如,在国际体育界,最近出台了新的规定,限制了一些 高睾酮水平 以及具有 XY染色体 的间性女人(intersex women)参加女子跑步比赛的权利,而不管她们作为女人的法律或社会地位如何,也不管她们是否从出生起就拥有其它女性性征(female sex characteristics)(世界田径 World Athletics,2019年)。体育监管机构(Sport regulators)假定(posit)这些规定是基于在社会考虑上(social considerations)所无法克服的关于性(sex)的生物真相(biological truths)。它们声称,具有 XY染色体 和 高睾酮水平 的女人(women)是“具有女性性别身份认同(female gender identities)的生物男性运动员(biologically male athletes)”(国际体育仲裁院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2019年,第71页)。这些说法得到了自称女性主义的评论员们的支持,包括前竞技运动员多里安·兰贝莱特·科尔曼(Dorian Lambelet Coleman 2019年),其说道:“当我们被告知,46,XY男性(46, XY males) [原文如此] 患有 DSD [“性发育障碍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的人认同为女性(female),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身份认同(identity)是最重要的,其效果是要抹去我们在赛场内外深刻的、重要的、性-特定(sex-specific)的经验/经历”。体育监管机构在反女性主义立场和排斥女人(women)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通过包括一个多世纪以来隐含地将次要劣等地位(inferiority)归赋(ascribing)于(所有)女人的身体(Erikainen,2020年)。然而,这种排斥在外(exclusion)对来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种族化女人(racialised women)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在许多方面是因为西方持久的话语预先将种族化(特别是黑人)女人及其身体定位为是非女性气质的(unfeminine),未能体现西方、白人和中产阶级形式的标准“女人身份(womanhood)”(Erikainen,2020年)。尽管如此,在强大的体育治理机构(sport governing bodies)和一些“性别批判”的女人权利倡导者之间出现了联盟(alliance)。其结果是,“生物”女性性质(‘biological’ femaleness)和“社会”女人身份(‘social’ womanhood)之间较旧的(older)、性别化和种族化界限的新迭代(new iterations)正在被划分出来(are being drawn)。然而,正是像科尔曼这样的女人权利倡导者抹杀了一个在女性主义(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义)政治中早已被承认的重要现实:没有单一的、共同的女性具身体现(female embodiment)经验或“女人身份(womanhood)”经验(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1983年;Koyama,本合集)——而且染色体和荷尔蒙都不能“决定(determine)” 性(sex)(Fausto-Sterling,2000年)。
跨儿女人和间性女人,特别是种族化的跨儿女人和间性女人,由于生物‘女性性质’(biological ‘femaleness’)的狭隘概念化(narrow conceptualisations),两者都面临着来自体育运动的更高程度的歧视以及排斥。最显著的案例集中在间性女人身上,最明显的就是卡斯特尔·塞门亚(Caster Semenya),她的女人身份(womanhood)自2009年以来一直受到公开质疑,这些质疑是以固有的种族化方式(inherently racialised ways)与她作为来自全球南方的“布奇(butch)【8】”黑人女人的定位交织在一起的(例如,见 Erikainen,2020年;Karkazis & Carpenter,2018年)。然而,跨儿女运动员也成为了“性别批判”媒体评论的对象。例如,在非自愿地披露了她的跨儿历史(trans history)之后,综合格斗运动员法隆·福克斯(Fallon Fox)与其它女人竞争的权利受到了公开质疑,包括同行竞争者公开评论她因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assigned male at birth)而可能具有的假定优势(presumed advantages)。媒体的报道包括着以生物还原论的(biologically reductionist)方式将她的身份认同(identity)病理化和边缘化的描述(Love,2019年)。
【8】此处复制译者在之前的译文中所使用的翻译注解:“butch”一开始指的是性别表达为在社会意义上被视为(socially-perceived)男性化(masculine)的女同性恋者,又译为“顶”,但如今其含义更指向女性式男性气质(female masculinity)(可见 Jack Halberstam 的同名专著),同样可理解为是以一种酷儿化的方式表现、展演男性气质(来自跨儿、非二元者、顺性别者等等)。此处采用“布奇”这一音译以避免性别身份的定式化导致窄化其含义。——译注
体育运动的例子正说明了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概念是如何被调动起来将一些女人(women)排斥在“女性性质(femaleness)”的范围之外的(另见 Karkazis & Carpenter,2018年)。通过诉诸“生物学”,权威当局宣称有着(lay claim to)科学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这种说法(claim)具有公众吸引力,即使几十年来它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受到质疑(例如 Haraway,1988年;Spanier,1995年)。然而,“科学”的权威允许关于 性差异(sex difference)的“生物真相(biological truths)”作为无可争辩的现实(incontestable realities)被呈现出来,并远胜过(仅仅是“社会的(social)”)性别(gender)。科尔曼等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与强大的体育权威当局之间的联盟,进一步表明了,将“生物学”作为跨儿者(和间性者)被排斥之基础这样的调动(mobilisation),在当前,是如何超越了传统政治定位关系(political positionalities)。此外,科学被策略性地使用,而不是被“事实性地(factually)”使用,以选择性(selective)的方式,使得排跨群体能够前置突出(foreground)TA们事先存在的(pre-existing)政治观点在某些“不可改变”之物上,即便性(sex)的不可改变性(immutability)本身是通过政治手段以话语方式建立的(established discursively)。正如哈伯德(Hubbard,1990年, 第15-16页)在三十年前所论述的,科学事实的世界是“语境性的(contextual),这不仅是因为它取决于我们是谁、在何时、在何地,而且因为它是由我们希望我们的‘事实(facts)’将我们带至何处所形塑而成的”。【9】 “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正在建构和调动非常特定的、具有争议的生物“事实”版本,而这也为反女性主义组织的政治提供了支持。
【9】 另见吉尔-皮特森(Gill-Peterson,2018年)关于跨儿和间性医学(trans and intersex medicine)的优生学历史的工作。
然而,重要的是要承认,我们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从中立位置写作,也不是为了这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合集。相反,在许多方面,就像我们所批判的排跨声音一样,我们是从一个既是政治的又是个人的定位位置(located position)来写作。我们是跨儿和多元性别(trans and gender diverse)女性主义者,并将个人的和身体的自主权置于中心作为不可妥协的价值,同时也以边缘化人群的陈述经验为主导留心着权力和不平等的结构(structures of power and inequality)。我们的写作视角是由我们自己的性别化历史(gendered histories),以及我们通过个人经历和教育轨迹而“进入(entry into)”关于性、性别和女性主义的“知识(knowledge)”(Hook,2005年,第23页)的情况(circumstances)所形塑的。继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88年)之后,我们将我们的写作概念化为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而承认情境性(situatedness)也意味承认着在政治上无辜清白(political innocence)的失败。我们的社会位置在认识上和政治上看都十分显著(epistemically and politically salient),因此我们不是“中立的(neutral)”观察者,也不是观察 TERF战争 的局外人。相反,这些“辩论”是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同事们和爱人们的生活/生命上和身体上进行的。这形塑了了我们校核整理接下来的文章的动机,也形塑了我们在介绍这本合集时集体发出的跨儿女性主义声音(trans feminist voice)。
本专题的概要(Outline of this monograph)
这本合集汇集了一系列经过同行评议的介入,其涉及女性主义内部(和外部)关于跨儿包容( trans inclusion)的复杂辩论。作为编辑,我们有意从多元角度寻求贡献。在一些观点上,投稿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彼此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并没有要求作者坚持依附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除了致力于承认跨儿者(trans people)的陈述经历值得尊重和认可。相反,联合这本合集中的论文,是对循证批判(evidenced critique)的承诺,以及对在跨儿与女性主义运动两者内部和两者之间建立真正的团结的关注(interest)。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些辩论的历史背景。第一部分,《巡览从过去到现在的女性主义》(Navigating Feminisms from Past to Present),追溯了女性主义和跨儿行动主义和思想(trans activism and thought)的交织历史,审视了这些历史如何形塑了学术研究、行动主义和更广泛的公共领域的当代辩论。
在《性战争和(跨)性别恐慌:当代英国女性主义的身份和身体政治》
(Sex wars and (trans)gender panics: Identity and bod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UK feminism)中,萨利·海恩斯(Sally Hines)通过审视女性主义思想的历史来解析当代英国的辩论。她探讨了“女人身份(womanhood)”的概念和关于女性主义的“适当”主体(‘proper’ subject of feminism)的辩论,重新讨论了女性主义对性/性别区分(sex/gender distinction)的概念化,从而将“基于性的权利(sex-based rights)”这一呼吁的出现置于脉络之中。海恩斯认为,这种方法否定了数十年来关于性(sex)之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评论,冒着将女人身份(womanhood)简化成生殖能力(reproductive capacity)的危险。她进一步坚持认为,当“女人身份”从“性”作为本质化的生物学这些问题中解脱出来时,它就会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范畴(productive category),从而使所有受到父权力量(patriarchal forces)压迫的人能够得到跨越不同的界限的拥护(allegiances)。
第二篇文章《本体论的女人:去验证、非人化和暴力的历史》(The ontological woman: A history of deauthentication, dehumanisation, and violence),批判性地剖析了“女人身份”的政治化结构(politicised constructs)——这些结构被用来证明将跨儿女人(trans women)排斥在女性主义之外是合理正当的。克里斯坦·威廉姆斯(Cristan Williams)着重于激发了数十年来的排跨政治(trans-exclusionary politics)的问题——即女人身份是自然/上帝赋予的,还是由一个人生活的物质条件所定义的。她描绘了排跨论点如何调动一种特定的修辞,以支持一种特定的道德,从而试图为有害的做法辩护。威廉姆斯最终认为,排跨个人和团体所付诸实施的道德观和做法对跨儿和女性主义社群来说都是有毒的(toxic)。
第三篇稿件是小山惠美(Emi Koyama)2000年的文章《到底是谁的女性主义?跨儿包容的辩论中不言而喻的种族主义》(Whose feminism is it anyway? The unspoken racism of the trans inclusion debate)的重印。史赛克(Stryker)和惠特尔(Whittle)(2006年,第698页)将其描述为“对蕾丝边-女性主义者(lesbian-feminists)以及跨性别活动家(transgender activists)的尖锐指责",因为TA们“将自己的论点建基在种族主义的做法和假设之上”。围绕着跨儿身份和身体的许多语言和话语,在著述撰写后的20年里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个由——对密歇根女人音乐节(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的排跨政策、以及跨儿异质性(trans heterogeneity)对白人中产阶级女人(可能是跨性/别也可能是顺性/别)造成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威胁进行批判性论述——所阐明的这个中心紧张关系(central tensions)仍然具有强烈的启发性。
在《女性主义将会是跨儿包容的或其将不会是:为什么两个顺性/别异性恋女人教育工作者支持跨儿女性主义?》(Feminism will be trans-inclusive or it will not be: Why do two cis-hetero woman educators support transfeminism?), 玛丽亚·维多利亚·卡雷拉-费尔南德斯(María Victoria Carrera-Fernández)和雷内·德帕尔马(Renée DePalma)解构了支持排跨意识形态的论点,并对跨儿女性主义和酷儿在教育方面的介入方法(trans feminist and queer approaches to education)提供了对比性的深刻洞见。卡雷拉-费尔南德斯和德帕尔马展示了学校如何作为社会化的媒介(agents of socialisation),将教育学(pedagogy )定位为是抗击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10】和性别化暴力(gendered violence)的有力政治工具。TA们不仅提出解放式教育学(emancipatory pedagogy)可以为创造更公平的社会做出贡献,而且还主张批判性酷儿教育学(critical queer pedagogy),其拒绝排斥性话语,并将跨儿经验纳入更广泛的女性主义教育议程中。
【10】可简单理解为假定异性恋是唯一的、正常的、规范的。——译注
本书第二部分《医学即政治》(The Medical is Political)在对跨儿经验是如何被定义与概念化的争论的语境下,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医疗“科学”(medical ‘science’)之间的关系。在《自我女性恋想(Autogynephilia):科学评论、女性主义分析以及替代性的“具身幻想”模型》(Autogynephilia: A scientific review, feminist analysis, and alternative ‘embodiment fantasies’ model)中,朱利亚·塞拉诺(Julia Serano)分析了自我女性恋想理论(the theory of autogynephilia)——根据这种理论,跨儿女人的性别身份认同是其性取向的副产品。文章列举了现有的大量证据来推翻这一理论,并说明了自我女性恋想(autogynephilia)如何被以及为何继续被反跨行动者(anti-trans actors)援引调用。为了对这些调动提出质疑,塞拉诺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alternative)“具身幻想”模型(‘embodiment fantasy’ model)以更好地解释被用来支持自我女性恋想(autogynephilia)的证据。她认为这个概念依赖于对女人(women)和LGBTQ+ 人群本质主义的、异性恋正统主义的(heteronormative)和性歧视的(sexist)假设,而这与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不一致。
下一篇文章《对“突发式性别不安”的批判性评论》(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rapid-onset gender dysphoria)推翻了“突发式性别不安(rapid-onset gender dysphoria ROGD)”这一概念,这是一个被适用于那些据称误认为自己是跨性别(transgender)的年轻人的伪科学式诊断类别。弗洛伦斯·阿什利(Florence Ashley)将 ROGD 作为一个类别的出现置于政治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并解构了——被用来支持其在学术语境内使用和支持其被诸如 4thWaveNow 等运动团体所使用——的证据基础和论据。阿什利认为,ROGD 反映了对科学语言的蓄意和政治化的武器化(deliberate and politicised weaponisation)以为了摒弃现存的大量证据——这些证据支持着以性别肯定之方式(gender-affirmative approaches)为跨儿青少年(trans teenagers)提供照料(care provision)。
罗文·希尔德布兰-查普(Rowan Hildebrand-Chupp)的文章《不只是“性别煤矿里的金丝雀”:对去过渡(detransition)之研究的跨儿女性主义方法》(More than “canaries in the gender coal mine”: A transfeminist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detransition)提供了在方法论上的洞见,为关于去过渡(detranitions)【11】这一令人焦虑话题的研究提供了启发。在跨儿/女性主义的辩论中,所有“阵营”的人都经常援引去过渡者(detransitioner)之形象,但学术研究几乎完全将去过渡人士(detransitioned people)自己的声音排斥在外。在许多跨儿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围绕着去过渡(detransition)的话语防御性(discursive defensiveness),由于担心那些暗示(或声明)TA们在过渡(transition)后感到反悔的个人们会被用来证明对性别肯定医疗服务(gender-affirming medical services)的使用权/机会(access)施加更大限制是合理正当的。希尔德布兰-查普通过剖析被归入“去过渡(detransition)”一词的概念来对付这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类别,以便当进行与去过渡相关的(detransition-related)研究时允许明确特异性(clear specificity)。通过批判性地介入去过渡(detransition)如何经常在研究(包括,并且尤其是,“跨儿积极的(trans-positive)”研究)中被糟糕地描绘(poorly represented),文章为一种叙事创造了空间,这叙事承认对于围绕着性别不遵从(gender non-conformity)和过渡(transition)的消极经验的促进因素的互相需要(mutual need)。
【11】“tranition”指性/别过过渡,“detranition”则指去性/别过渡。【原文复制于译者之前写的脚注:读者需注意,不能将“transition”唯一理解成药物过渡或进行相关的手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过渡方式(跨儿出柜也是一种过渡)】但,很可惜也没办法的是,在 Hildebrand-Chupp 的文章中 “tranition”只指药物过渡/手术过渡相关行为。——译注
第三部分《当代话语、辩论、以及跨儿女性主义反抗》(Contemporary Discourses, Debates, and Transfeminist Resistance)转而讨论当下关于女性主义行动主义与公开论战(feminist activism and contestation)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取决于主要在西方英语语系国家展开的辩论,但通过后殖民背景下不平等的知识等级结构(unequal hierarchies of knowledge),其影响远远超出这些国家之外。这一点在《忽视与危险:奇玛曼达·苟兹·阿迪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和跨性/别(以及顺性/别)非洲女性主义者的声音》(Disregard and danger: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nd the voices of trans (and cis) African feminists)一文中有所体现,B·肯明加(B Camminga)在文章中说明了英国电视台提出的一个问题所带来的后果(consequences)是如何传遍非洲大陆引起反响的。肯明加探讨了对——尼日利亚女性主义者阿迪切(Adichie)在电视上提出的跨性/别女人不是女人——的回应,并展示了这如何导致媒体的强烈兴趣,在此期间,非洲跨性/别女人的声音是被抹去的。肯明加试图放大这些跨性/别女人的声音,质疑阿迪奇对“女人身份(womanhood)”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似乎与非洲国家的跨性/别女人和顺性/别女人(both trans and cis women)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ies)并不相符,而这也表明了全球北方和南方(Global North and South)之间女性主义话语的不平等流动(unequal flow)。
下一篇文章《厕所辩论:阻碍跨儿可能性和捍卫“女人受保护的空间”》(The toilet debate: Stalling trans possibilities and defending “women/s protected spaces”),细想了性别隔离(gender-segregated)公共厕所如何成为“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女性主义者们辩论和政治化的重要场所,TA们将女人公共厕所(women’s public toilets)定位为顺性/别女人(cis women)的安全空间,并反对跨性/别者(trans people)使用性别隔离厕所的权利。夏洛特·琼斯(Charlotte Jones)和珍·斯莱特(Jen Slater)利用“厕所周围(Around the Toilet)”研究项目的数据,该研究项目探讨了厕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安全和无障碍的空间,进而TA们展示出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所政治化为是对顺性/别女人而言的安全空间,其本身如何变成了对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人群(trans and non-binary people)来说的危险场所。TA们认为,排跨政治和做法(trans-exclusionary politics and practices)对改善厕所之使用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跨性/别者(trans people)面临更大的暴力风险,并助长了“女人身份(womanhood)”的有害同质化(harmful homogenisation)。
在第十篇文章中,《性工作废除主义和霸权女性主义:对来自巴西的性别多元化的性工作者和移居者的影响》(Sex work abolitionism and hegemonic feminisms: Implications for gender-diverse sex workers and migrants from Brazil)卢·达·莫塔·斯塔比莱(Lua da Mota Stabile)审视了西方激进女性主义围绕着性工作和人口贩运的话语论述对来自全球南方的跨儿性工作者和性别多元化性工作者(trans and gender-diverse sex workers)造成的后果影响。她以移居到欧洲的巴西性工作者为重点,探讨了西方女性主义如何经常以再生产重现(reproduce)殖民主义、顺性/别性歧视(cissexism)和种族主义的方式来描绘(represent )移居性工作者(migrant sex workers)。同时,西方女性主义政治影响了国际反人口贩运(anti-trafficking)和反卖淫(anti-prostitution)的话语论述,对跨儿性工作者和性别多元化性工作者产生了负面影响。 达·莫塔·斯塔比莱论证了承认性工作者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能力和良知的重要性,并提议制定(development)——能够接受移居者,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的弱势群体——的监管与权利框架(regulatory and rights frameworks)。
最后,在《跨儿女性主义者与自由派机构:一个爱情故事》(The transfeminist and the liberal institution: A love story)中,杰伊·伯纳德(Jay Bernard)对TA所制作的“激进女性主义/跨儿:一个爱情故事”(RadFem/Trans:A Love Story)活动所收获的经验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该活动是 BFI Flare London LGBTQ film festival 电影节的一部分。TA考虑了交涉协商(negotiating)激进的跨儿女性主义政治(trans feminist politics)和自由派文化机构(liberal cultural institutions)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默认的做法是不站在(政治的 political)一边。TA反思了表征(representation)、排斥(exclusions)和包容(inclusions)的问题,以及TA自己和其它人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s),为巡览(navigating)和超越(transcending)敌对政治(antagonistic politics)提供了经验教训。
横跨这些介入,我们的目的是推进对TERF战争的理解、它们在女性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位置,以及它们与“科学”的关系。虽然我们并不声称要解决这个多层面领域(multifaceted field)的每一个辩论话题,但我们的目标是为阐明在女性主义社群和跨儿社群内的排斥性话语(exclusionary discourses)做出贡献。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些根深蒂固的关于“排跨(trans-exclusionary)”政治和“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政治的辩论将变得完全无关紧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绕着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为所有人争取性解放(sex liberation)和女性主义自由(feminist freedom)。
致谢(Acknowledgements)
我们感谢 Steven Brown 以及《社会学评论》的审稿人们,感谢TA们对本文早期草稿提出的有用评论。
基金(Funding)
该奖学金部分由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支持(基金号码 209519/Z/17/Z)。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因豆瓣篇幅限制将放在评论中。
作者简介(Author biographies)
鲁思·皮尔斯(Ruth Pearce)是利兹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的访问研究员。她的作品从跨儿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了不平等、边缘化、权力和政治斗争等议题。鲁思是《理解跨儿健康》(Understanding Trans Health)(Policy Press 出版社, 2018年)一书的作者,以及《跨儿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Trans)(Routledge 出版社, 2020年)一书的联合编辑。她在博客 上记载自己的工作和兴趣。
Ruth Pearce is a Visiting Researcher in th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Her work explores issues of inequality, marginalisation, power, and political struggle from a trans feminist perspective. Ruth is the author of Understanding Trans Health (Policy Press, 2018), and co-editor of The Emergence of Trans (Routledge, 2020). She blogs about her work and interests at .
索亚·埃里凯宁(Sonja Erikainen)是爱丁堡大学生物医学,自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TA的跨学科研究侧重于围绕着生物医学和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和伦理议题。TA的研究和出版物涵盖的领域包括性别和体育科学、科学和流行文化中的激素,以及科学的允诺未来。TA是《性别验证和体育中的女性身体的形成:关于现在的历史》(Gender Verifi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ale Body on Sport: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作者(Routledge 出版社,2020年)。
Sonja Erikaine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Centre for Biomedicine, Self and Society, where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cuses on social, historical and ethical issues around biomedicine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ir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cover areas including gender and sport science, hormones in scientific and popular cultures, and the promissory futures of science. They are the author of Gender Verifi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ale Body on Sport: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20).
本·文森特(Ben Vincent)(代词 they/them)拥有利兹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前在剑桥大学获得生物自然科学和跨学科性别研究的学位。TA的第一本书《跨儿健康》(Transgender Health)在英国医师协会(BMA)医学图书奖上获得高度评价。TA是《非二元性别:巡览社区、身份和医疗保健》(Non-Binary Genders:Navigating Communities, Identities, and Healthcare)的作者,也是《非二元生活/生命》(Non-Binary Lives)合集的共同编辑。可以在线上通过 Twitter 账号 @genderben 找到TA。
Ben Vincent (they/them) has a PhD in Soci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which followed degrees in biological natural sciences and multidisciplinary gender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ir first book, Transgender Health, was highly commended at the BMA Medical Book Awards. They are the author of Non-Binary Genders: Navigating Communities, Identities, and Healthcare, and co-editor of the collection Non-Binary Lives. They are online via @genderben on Twitter.
*本文其中两位作者所使用的代词为“they/them”,译者仍使用“TA”作为翻译,但译者认为“祂”也可以作为单数“they/them”代词的翻译











